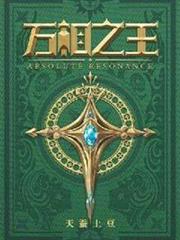贪吃蛇若是换了旁人定然不会自报家门,然而面前的黑衣人好似并没有打算掩藏身份,他低沉平静的声音在众人耳畔响起,犹如惊雷炸响:
“九衢司正四品指挥使,萧犇!”
萧犇?凉王的人?!
燕东楼闻言瞳孔微微收缩,他勒紧缰绳按住躁动不安的坐骑,沉声道:“萧大人,虽然我不知道你深夜出来有何贵干,但你护着的那人乃是诚王指名道姓要的死囚,身犯株连之罪,你莫不是要与朝廷作对?!”
“诚王恐怕还代表不了朝廷。”
萧犇语罢拉下脸上的面罩,转头看向那名被追杀的青衫士子,只见对方身上满是斑驳的血迹,此刻正痛苦捂住右手蜷缩在地,细看已经断了一根食指,将来恐怕是再也不能写字作画了。
萧犇淡漠开口:“崔先生,又见面了。
准琅为了躲避追杀早已筋疲力尽,此刻更是被疼痛折磨得浑身颤抖,他闻言艰难睁开双眼,这才发现救了自己的人是萧犇,忍不住错愕出声:“萧萧统领?”
萧犇料定了燕东楼等人不敢阻拦,语气有恃无恐:“随我走,凉王命我带你入宫面圣。”
崔琅又是一惊:“为何?!”
萧犇静静注视着他,那双眼在漆黑的夜色中亮得惊人,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让崔琅心中积压多年的山石瞬间轰塌:
“凉王已向帝君阐明元安十五年科举舞弊一案,带你入宫,自然是要还你公道。”
虽已春至,夜色犹寒。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踏过长街,朝着皇城的方向而去,寒风刮过面庞,犹能闻到雨后的泥土腥味,仿佛预示神京即将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风雨。
换做往常这个时辰帝君早就歇下了,今夜玄华殿内却是处处点灯,彻夜长明,只见他身着常服坐在高位,内侍宫女站立两旁,玉阶下方跪着泾渭分明的三拨人。
一拨是早已致仕的内阁老臣陈孟延和其子陈朗。
一拨是草草处理过伤口的崔琅以及陪同在旁的萧犇。
另外一拨则是诚王楚圭不,说是一拨也不恰当,毕竟只有他一个人。
“哗啦一一!”
有宫女心惊胆战上茶,帝君却看也不看,脸色阴沉的拂袖一挥,茶盏瞬间落地碎裂,让下方跪着的众人愈发噤若寒蝉。
最后是陈孟延率先支撑不住,拖着老迈的身躯膝行上前,向帝君颤颤巍巍哭诉道:“陛下,老臣为西陵尽忠职守数十年,从未有过私心,如今无凭无据,怎可听信崔琅的一面之词便断定老臣当年徇私舞弊,恳请陛下明查呀!!”
他尚能沉得住气为自己辩驳,身旁的儿子陈朗却早已是面色发青,大脑一片空白,毕竟谁也想不到数年前的旧事还能被重新翻出,崔琅一个寒门书生居然也真的有本事上达天听。
“查?朕自然是要查的。”
帝君威严低沉的声音在大殿之中响起,引发阵阵回音,就如同暴风雨即将来临前的海面,看似平静的表象之下是足够吞噬一切的汹涌暗潮,冷笑着道:
“朕不止要一个个查、仔细的查!还要将当年经手此事的官员一个个挖出来,将当年参加科举的落榜士子一个个寻回来,看看你陈孟延是不是真的吃了熊心豹子胆,居然胆敢行此株连之事!!”
随着最后一个字音落下,帝君“评”的一声重重拍在御案上,隐忍多时的怒气终于忍不住在此刻爆发,厉声命令道:“速命户部将元安十五年负责主持会试的官员名单悉数调出,致仕者重新召回,在朝者连夜进宫,就连那些士子也一个都不许落下,哪怕散落在天南海北也必须给朕全都找回科举,那是什么?那不仅是皇权对抗世家门阀的手段,更是替朝廷筛选治世之才的根本,如今却被这些所谓的天子近臣暗中操控,徇私舞弊不知有多少英才被酒囊饭袋所替!
帝君先是震惊,随后是愤怒,更多的却是无尽的心痛,如今西陵外敌未平,尚有内忧,自己身边亲近的臣子居然就敢做这种毁国乱政的事,并且还是元安十五年的旧事,焉知这些年又有多少像崔琅一样的举子被权贵所害?!
此刻没有任何人敢承受高座上那名帝王的滔天怒火。
夜色尚且浓稠,宫门便已大开,先后有数百名鸿翎急使手举火把策马离京,扬起烟尘滚滚。户部尚书孔道明,太常寺少卿独孤涯,内阁大学士江镜堂,另还有六部之中当年经手主考事宜的大小官员尽数被宣召入宫,一时间风声鹤唳,惹得人心惶惶。
那些尚在睡梦中的王公贵族也被这阵动静惊醒,纷纷派出家丁仆役前去打探,然而皆是一无所获,只能坐立不安等待天明,暗自猜测宫内莫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元安十五年的春闱共有三百一十五人上榜,答卷皆在东华楼内封存,然而那年参加会试的举子共有上千人,每人答三场,一考四书义,二考诏诰表,三考经策史,所有答卷加起来怕不是有接近上万份。
而且帝君要的不止是这些,他还要看一名祖籍江州,姓崔名琅的考生从乡试开始的所有答卷,近乎数百人秉烛夜照,在东华楼内疯狂翻找,只恨爹妈给自己少生了几条胳膊。
今夜皇城之内风云变色,所有风波皆因楚陵的一封奏折而起,然而他却称病未去,毕竟他说过,不会再见崔琅,更何况有些事起个头便好,不必置身其中。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玄华殿内的夜色仿佛永无尽头。
诚王楚圭垂眸跪在台阶下方,已经算不清自己跪了多久,膝盖从一开始的疼痛冰冷到酸麻僵硬,到现在已经失去了知觉,帝君却从进殿开始就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仿佛早已忘记了这个儿子的存在。
但楚圭并不焦急,他此刻只希望父皇真的把他忘了,忘得越远越好,千万不要让陈孟延引起的怒火烧到自己身上。
此刻玄华殿内的地上铺满了密密麻麻的考生答卷,几名博学鸿儒坐在矮桌后方,借着烛火挨个验看那些落榜举子当年的答卷,凡遇精彩文章便呈上御前,而其余的小官则没这种待遇了,一个个撅着屁股趴在地上挨个翻找元安十五年的卷子,然后收录集合呈给那些大儒。
这大殿之中,有人坐着,有人趴着,但还有些人是跪着的,只见当年和陈孟延同流合污的大小官员全都胆战心惊地跪成一团,明明身旁就燃着炭盆,冷汗还是从后背一点点冒出,浸透了身上或红或蓝的官服。
完了,这下是真的完了!
这几乎是所有人脑海中一致的念头。
就连一开始气定神闲的陈孟延也有些跪不住了,他眼见一份又一份的考卷被呈上御前,心也越坠越深,那些人都是他当年亲手罢选的,文章水平如何他自然清楚,圣上一看便知,这下都不用严刑拷打,傻子都知道里面有猫腻。
“陛下!陛下!臣有罪啊!”
终于有人熬不住了。
只见一名绿袍官员惶惶如丧家之犬,连滚带爬脱离身边的同伴上前,跪在地上向帝君痛哭流涕叩首道:“崔琅所说确有其事,当年有二十六名学子本可名列甲榜,却因才学压过陈朗而被当时的陈孟延陈大人罢选,乙榜有二十二名学子被人所替,一个名额卖到白银万两,六部之中皆有官员经手,微臣该死,迫于威势不敢直言,也曾受贿千两,如今愿意将功折罪把名单悉数供出,恳请陛下从轻发落啊!!”
这种事便如同船底破洞,来了一个后面的就堵不住了。
当年科举舞弊的官员见有同伴叛变,顿时心中一慌,生怕自己吃亏,连忙跟着爬上前道:“陛下!陛下!臣也愿意将功折罪!”
“陈大人当年写了亲笔密函,微臣如今还藏在家中!”
“陛下,臣不曾收受贿银,也不愿参与其中,只是当时令狐大人他们以妻儿性命威胁,迫不得已才为之啊!”
然而任由他们如何哭喊跪求,高座上的帝王始终一言不发,他一张张翻看那些落榜考生的答卷,再一张张对比那些上榜者的答卷,惺松不定的烛火在脸上投落一道阴影,看起来喜怒难辨。
“哗啦一一!”
不知过了多久,帝君忽然将手中摞答卷奋力扬下台阶,不偏不倚刚好砸在陈孟延的头上,明明没有多大的力道,后者枯朽如木的身躯却控制不住在翻飞的纸张中跌倒在地,整个人如遭雷击。
“陈孟延!你好大的狗胆!这些被罢落的考生文章才学不知强过甲榜多少,当年竟都被你强行压下!朕将你当做心腹之臣,你便是这样报答朕的吗?!你们陈家满门有几个脑袋够砍的?!!”
陈孟延前面的时候还能勉力支特,在听见最后一句话的时候终于支撑不住,眼睛一闭晕了过去,六神无主的陈朗连忙接住他的身体慌张喊道:“爹!你怎么了?!爹?!”
可惜他从小濡慕的父亲这个时候已经救不了他了,堂下所有人都在哆哆嗦嗦祈求神佛保佑,保佑自己可以渡过眼前这场难关。
帝君从龙椅上站直身形,望着外间逐渐亮起的天色缓缓吐出一口气,脸色阴沉的命令道:“来人,将犯事官员一干人等通通带下去诏付有司详查,朕给你们五天时间,务必将当年的枝叶末节给朕查得水落石出!!”
“诺!!”
外间的侍卫声震大殿,立刻领命而入,将那些官员死狗般拖出。
此刻黎明破晓,一轮红日从宫墙外间缓缓升起,驱散了无尽黑暗,那些官员却个个如丧考妣,心如死灰,他们很清楚,这或许是自己这辈子最后一次看见太阳了。
崔琅是蒙冤者,帝君虽未将他关押,却也派了专人将他暂时看管在皇宫,临出殿门前,帝君的视线在他右手那根断指上停留片刻,暗沉的眼底悄然闪过一丝惋惜一一可惜了,西陵有规矩,身有残缺者不得为官,更何况断的还是食指,将来提笔握字都难,否则还能给崔琅一个官位补偿当年之事,如今错失,只能说时也命也。
萧犇本来是奉了楚陵的命令才将崔琅带回宫中面圣,他向帝君阐明因由之后也准备离开,但没想到走下台阶之时身后忽然响起一道沙哑颤抖的声音,下意识顿住了脚步。
“萧统领”
只见崔琅披头散发,脸上满是泥污血痕地朝萧犇踉跄走来,他紧紧捂着包扎过的右手,再也看不出曾经风度翩翻翩的样子,唇瓣干裂出血,几经迟疑才哑声问道:
王爷他他还好吗?”
王爷?
萧犇心想王爷挺好的,这个时候和世子估摸着还没醒呢,但他回忆起自己临出门前楚陵的叮嘱,到嘴的话又改了口风:“不大好,王爷昨日又吐了两口血,病得起不来床。”
准琅闻言再也支撑不住,双膝一软跪在地上痛哭出声,却不知是哭自己愚蠢跟错主子,还是哭自己辜负了一个挚友:“我是个罪人!罪人呐!!
不仅差点害了王爷,还害得母亲被楚圭牵连杀害,我真是万死也难赎罪孽!!”
当日他离开凉王府后便想带着母亲隐姓埋名离开京城,不曾想赶到茅屋时只见满地血迹,母亲早已被楚圭派去的杀手灭口,若不是萧犇相救,只怕他也要命丧刀下。
萧犇盯着他看了许久,却冷不丁开口道:“你母亲没死,如今正在城中处民宅安身。”
崔琅闻言一怔,抬起通红的眼睛震惊看向他:“这…这怎么可能?!我去时明明看见满屋鲜血,母亲早已被人推落山崖,树枝上还挂着她的衣服布料!”
萧犇淡淡道:“那是我故意弄出的障眼法,王爷猜到事败之后诚王必会迁怒你的母亲,便命我暗中保护将她平安救出,待科举舞弊案了结后,将你二人隐姓埋名送往他乡,免得遭人报复。”
如果说崔琅一开始还能勉强支撑住身形,到最后却是再也没了力气,整个人失魂落魄跌坐在地,他红着眼睛看向萧犇,唇瓣无措动了动,嗓子暗哑得几近无声,说的却是:
“为什么”
为什么?
他害楚陵至此,对方为何还要不计前嫌帮他?
崔琅本以为自己那颗被世道磋磨狠了的心再也不会相信情义这种可笑的东西,楚陵所做的一切却又在疯狂动摇他的认知,心中仿佛发生了一场寂静无声的山崩,倾覆了什么唯有他自己知道。
“没有为什么。”
萧犇仍是那副面无表情的死寂模样,好似世间任何事都不能引起他的情绪,语气平静:
“其实你如果早些将此事告诉王爷,他就算与那些世家门阀为敌,今日拖着病体也会来金銮殿前替你讨个公道。”
萧犇说着顿了顿:“可你没有.
他这四个字声音很轻,却如同一击重锤落下,将崔琅晕头转向,喉间甚至泛起了血腥味。
“你觉得他善,你觉得他忍,所以你从来不认为他这么与世无争的性子会为了你们与朝堂上那些人发生冲突,所以你宁愿相信诚王会给你想要的一切,也不愿相信王爷会还你一个公道。"”
所以今日来玄华殿中的只是萧犇,而不是楚陵。
所以那封奏折只是为了还天下寒门士子一个公道,再也不是为了崔琅这个人。
萧犇提剑缓缓步下台阶,莫名想起他当年十五岁不到就被帝君指派给楚陵当贴身护卫,后来因失口提起过逝的月贵妃犯了宫中大忌,被帝君下令杖毙,那时他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毕竟他从来没想到那个对帝君谦恭谨慎至极的的王爷,居然会为了一个下贱的侍卫在玄华殿里跪求三个时辰,只为请帝君收回成命。
准琅那些人从来都没看懂过王爷“噗一一!”
萧犇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身后陡然传来崔琅失态吐血的声音,以及宫女惊慌失措的呼喊,然而最终都随着他逐渐远去的步伐消失在风中。
直到此刻崔琅才终于明白自己背叛了什么、辜负了什么、错失了什么。
不止是十年寒窗,不止是长书万卷,不止是圣人之言。
还有世上唯一一个以诚待他的挚友,一个值得满府谋士追随的明主,那是天下所有士人的毕生所求。
可如今顿成云烟,都没了…
都没了.…
准琅生平第一次知道万念俱灰是什么感觉,他茫然抬头看向上空,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身形控制不住晃了晃,最后轰然一声晕倒在地。
这次他再也没能爬起来。
一团暗沉的、如同鲜血凝结的红云缓缓出现在皇城上空,仿佛随时会落下一场铺天盖地的血雨。那是属于崔琅的痛苦,有前半生苦读的心酸,有后半生怀才不遇的愤怒冤屈,更多的却是自己辜恩负义,道心尽毁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