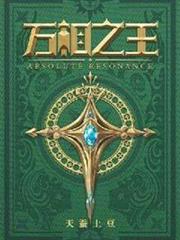第二十七章
常意欢是见过苟妙菱的一一就在不久之前,在她与青岗宗的姚相顾切磋之时,凌霄台上的窥天镜将二人比斗的过程展现给了许多人看。
当时,在流云榭内坐着的是仙门百家的代表长老与核心弟子。
青岚宗虽然家大业大,为所有来参与秘境历练的弟子都准备了一场宴席来招待,但流云榭毕竟空间有限,他们还启动了许多别的建筑来待客。
而常意欢作为灵崖山门主之女,自然是跟长老一起被邀请至流云榭入座宴饮的。
而阎固等人,因为不是灵崖山的核心弟子,没有去成流云榭,自然也没有见证那场人榜第一、第二筑基的比斗。
他只知道,归藏宗的荀妙菱刚刚升入筑基境就被排为人榜第一,青岚宗的弟子不服,向之发起挑战,却也输得彻底。
荀妙菱的天才之名响彻仙门百家。
但这和阎固这种小人物有什么关系?
上三宗的天才海了去了,每隔几年就要出个天才或者怪胎。
但正因这些事情离阎固过于遥远,导致他连关注的兴趣都没有。
他对所谓的“人榜第一筑基”没有太多嫉妒之心,但也升不起任何的向往之情。他只是在这庸碌尘世中挣扎的一只蚂蚁,关心的是如何争取更多的修行资源、如何把机缘带来的收益最大化。
他进入秘境之后,阴差阳错之下,叫他在第一天就遇到了一对炎凰鸟夫妻,更巧的是它们的蛋还并未孵化。
若能与一只雏凰结契,那将给他的修行带来莫大的助力。
原本他是只想带走一只雏凰的,但这次还有一向仰慕他的梦华师妹同行。当时的阎固心想,这样也好,就由师妹去引开成鸟的注意,他伺机把蛋偷走,事成之后大不了他与师妹一人一只雏凰鸟,也算皆大欢喜;若是不成,但至少他承担的风险大大降低了。
没想到最后不仅折了梦华师妹,连他自己,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而他的师姐常意欢虽然性格暴躁,但也好面子、护短,加上她与梦华师妹一向关系亲密,借她之手惩戒那两个剑修本是十拿九稳的一“荀妙菱?!"
常意欢用仿佛见了鬼般的神色看着面前那个提着笼子的少女,脸上一阵青一阵白。
同时,阎固脸部的肌肉一阵紧绷,似乎浑身上下的肌肉都僵硬住了。他不可置信地、用发颤的语气问道:“师、师姐,你叫她什么?”
“她是归藏宗的荀妙菱!”常意欢深吸一口气,猛然扭头盯着他,眼中的冷漠令阎固暗自心惊,“你说荀妙菱抢走了你的两只雏凰?”
阎固的牙关已经开始打冷颤。但事已至此,他只能一口咬定:“是。”
他说的也不全是假话。荀妙菱与她身边的那个白衣青年是强行从他怀里带走了那两只雏凰!
“荒谬!”常意欢恨铁不成钢地甩了甩鞭子,以乎很想再往阎固身上来几下,但顾及有外人在场,硬生生忍住了,“就凭你那点修为,也配与荀妙菱抢?”
阎固微微瞪大眼,居然微微愣住,几秒后才回过味儿来,脸直接涨成了猪肝色。
“就算…就算她是归藏宗的亲传弟子,那也不能随意欺压其他门派的修士吧!”
常意欢烦躁地道:“她仅仅是归藏宗亲传这么简单吗?那是我们修真界的第一筑基!你,我,我们灵崖山这次来参加历练的弟子全都绑一块儿吧,可能还不够人家打的!”
说着,荀妙菱已经提着笼子走近了。她笑眯眯的,像是个用玉雕成的人,眉目里有种不沾尘世的清澈与纯净,怎么看也不像是那种恃强凌弱、目中无人的性格。
但修仙界的人,光看外表哪个不是仙气飘飘、气度非凡?大家都善于伪装。
常意欢勾起一个尴尬的笑容,礼节性地作揖道:“荀道友。抱歉,昨晚我探查到了这个与众不同的迷踪阵法,一时好奇,送出了不少灵兽去探查,看来是打扰荀道友了。"绝口不提她是带着人打上门来算账的事。
荀妙菱恍然般地点点头,也没说信还是不信,视线在灵崖山的几个弟子身上转了一圈,最终不出所料地停留在了阎固身上:“这位道友,你看起来有些眼熟。”
“啊,我记起你了一一那时你抛下那受伤的女修,头也不回地御剑走了。当时,我和我姜师兄还纳闷,你是不是正在遭什么人追杀,逃的那么快呢。”
几人间的氛围有一瞬间的凝滞。
阎固头皮发麻。
他后退一步,下意识瞥向常意欢。
果然,他常师姐已经是满脸的阴沉之色,似乎恨不得将他抽筋剥骨。
“这、都、是、误、会。”常意欢冷笑一声,一字一顿道,“我师弟呢,对我那梦华师妹最是痴心。当时他恐怕是吓坏了,才导致的言行失据、慌不择路,但他的目的,应当是为了跑来向我求助,让我救救师妹.阎固,你就说是不是?”
“是、是。”阎固忙道,“我对梦华师妹痴心一片一一”
下一秒,只见常意欢皓腕上的赤色珊瑚镯子一动,化为一只鳞片细密的赤红小蛇,轻嘶着吐出蛇信,眨眼就窜入了阎固后颈的衣物之中。
“啊!师、师姐!师姐烧命!”
“阎固,你对梦华如此痴情,那想必是伤在她身,痛在你心。既然如此,我就尽师姐的职责帮你痛上痛,也算是满足了你的夙愿!”
“呃,我的心好痛啊!”
阎固脸色煞白,在地上不住翻滚着。灵蛇的毒素很快发作,他的双唇逐渐透出暗沉的青黑色。
他惊恐地在自己的衣襟中不断搔抓着,但那条赤红小蛇却已经不慌不忙地爬了出来。常意欢微微俯下身,小蛇乖顺地爬回她的掌间,在手腕处盘好,光芒一闪,又化为了原本的镯子阎固跪倒在地,伸出双手去抓常意欢的裙角:“我错了,我错了!师姐饶命,饶命啊师姐一一我虽欺骗了您,但我罪不至死啊!
常意欢笑道:“现在是不是体会到心痛的感觉了?”说着,她一脚把他踢开,居高临下道,“你现在就自己毁去腰上的信物,回船上找长老要解药。这毒不至于要了你的命,但会让你气血瘀滞,灵穴受阻,再也无法使用灵力。你继续挣扎也是无用的。
“至于你的"痴心"么,等我们所有人回了灵崖山,再做处置吧。”
常意欢在灵崖山弟子中的威严毋庸置疑。
她这一番决定,没有任何灵崖山弟子跳出来为阎固鸣不平,他们甚至脸色都没怎么变化。
阎固迟疑了一会儿,眼看局势已经无可转圜,他低下头,强压下眼中的怨愤,伸手解下自己腰间的金螺重重碾碎。
下一秒,他的身影瞬间化为流光消失在原地。
处置完阎固,常意欢狠狠松一口气。她略带愧疚地转过头,对荀妙菱说道:“荀道友,今日是我收门内弟子蒙蔽,险些被他利用和你们对上,还望你不要介怀。”
“哪里。”
荀妙菱也不管常意欢到底是因为归藏宗的势力低头,还是真的相信她的为人,但至少对方已经主动解决了阎固这个麻烦。
她把手里的藤笼递过去:“这些灵兽都是道友你的吧?长得挺可爱的。”
常意欢接过那个笼子,刚想谢谢荀妙菱的夸赞一一毕竟她也是这么觉得的,长相不堪的灵兽很少能得到她的青睐。但下一秒,她就听懂了那些泪眼朦胧的灵兽心中所想:
主人!这两个人好可怕!
我们差点被吃了呜呜呜呜!
“”常意欢沉默。
她不禁开始思考荀妙菱口中的可爱”是不是有另外一重意思。即看着很好吃。
常意欢和荀妙菱道了声别,随后带着自己的灵兽头也不回地跑了一一那背影好像透着一种莫名的慌张。
临走前,她还给苟妙菱和姜羡鱼一人留下了三根引兽香。据说这是以他们灵崖山的独门秘法所制的香,只要点燃,就能做引兽之用。无论是把要捉的灵兽诱出来,还是探索巢穴时需要调虎离山,都非常好用。
荀妙菱打量着那三根绿色的细香,半信半疑,将之收入了储物法器里。
她和姜羡鱼继续御剑赶路,慢慢靠近秘境更深处的地带。
慢慢的,脚下触目可及的土地变得更加湿软,树林间也出现了密集的水洼。明明是白日,周遭的光线却更加昏暗,树木变得更加张牙舞爪,枝干上缠绕着的藤蔓和苔藓也如一片片绿锈般布满了。
水洼如同一面镜子,倒映着灰暗的天色和斑驳的树影。视线内漂浮着层薄雾,那雾是一种潮湿而略带腥味的气息。
“这里灵气充裕,树木长势极盛。但倒没几只灵兽的踪影。”荀妙菱环顾四周道。
按理说,越接近秘境的核心,遇上的灵兽就越是强大、危险,越要谨慎小心。
但这里却太安静了。
他们御剑而过,在深绿色的水面上投下两片阴影。
突然,水面泛起一阵涟漪。
噗通!
一只体型巨大的鳄鱼从水中跃出,张开血盆大口,直直咬向荀妙菱的衣角。
一道灼目的光芒闪过。苟妙菱一张符甩出去,雷光在鳄鱼嘴中陡然炸开。一阵黑烟过后,它痛苦地扭动着身体,转身潜入水中逃走了。
接着又是第二只,第三只。
荀妙菱不断往外甩着符咒,姜羡鱼则分化出剑气补刀。
繁密的树冠如乌云般盖在头顶,而他们御剑和水面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近。
姜羡鱼的“齐物我”昨天才刚发动过一次,冷却时间还没过去。他沉思一秒,回头道:“你手上的符还有多少?”
荀妙菱手上最后一张火球符纸丢完了,灵光一闪,出现了一沓足有半掌厚的火球符:“符咒管够。你要丢几个玩玩吗?也能省点灵力。”
姜羡鱼低头看了眼那些符纸:
在这种地方还是别用火符了。”
荀妙菱画的火符他是知道的,一不小心就会炸成一片火海。放火烧山,牢底坐穿啊。
“事已至此,那就只能来硬的喽。”荀妙菱一挥手,灵剑飞至她手中,她驾驭着灵气使自己短暂浮空,汇聚灵力于剑身,息心剑上溢出点点星尘般的莹光,似乎在为主人的战意而轻颤一一荀妙菱挥剑向前中斩去。
一道明亮至极的剑光从剑尖迸发而出,如同一道弧月斜着划破天际。
剑气所过之处,空气爆发出尖锐的呼啸,周围的树木被巨大的风力所吹动,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树冠在剑气的冲击下整整齐齐地断裂,无数枝干混合着绿叶和碎片,纷纷扬扬地从空中坠落,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
再抬眼看去,视线已经宽敞多了,他们御剑也能升到更高的地方了。
因为荀妙菱一剑把头顶那些碍事的枝冠全给削了。
姜羡鱼:"”
虽然动静大了些,但很好的解决了问题。
窥天镜外的长老们看见这一幕,纷纷无语。
有个长老叹息:“她是生怕别人不知道她在这儿啊。”
许多实力不太行的修士,或者是不想惹事的修士,在秘境里活动的时候多少有些偷偷摸摸的。毕竟谁都说不准他们会不会遇见什么打劫的团体,或者是因为觊觎宝贝而下手争抢的人。
再不济,也就是平平常常地参加历练,看见人不卑不亢地打个招呼。
不像荀妙菱,她一剑至少声震周围五里,这下大伙儿都知道这儿有人了。
但她的高调偏偏是刻意理解的一一因为她的实力就是底气。别说她身边还跟着一个筑基后境的姜羡鱼寸步不离地给她“护法”,可以说荀妙菱是所有人最不想挑战的修士之一。
但荀妙菱闹出的动静还是得到反馈了的。他们刚御剑飞出没多远,忽然听到一声焦急的喊声:
“一一救命,有人吗!救命啊!”
呼救声断断续续,似乎来自不远处。但被越来越浓的雾气模糊化,很难把握距离。
荀妙菱和姜羡鱼对视了一眼,双双御剑冲进雾气深处。
远远的,他们勉强看见一个人的轮廓在水中挣扎。凑近了发现,那是个年轻的女修,大半个身子已经陷入了沼泽里,泥浆几乎要没到她的胸口。
“两位道友…救救我!”对方发髻散开,乌发如云覆在身后,颊上沾的泥点更显她的肌肤白皙无瑕,“我、我在追击一只灵兽的时候不慎落入沼泽中,连储物法器也丢了,若不是遇上你们,恐怕真的要困死在这里.…
困死倒也不至于。
只是被强制禁锢几天罢了。等时间到了自然会被秘境的传送机制送走。
其实,据说秘境中有不少和这类以的禁锢陷阱。但不想浪费时间的直接敲碎手上的信物、传送走也就罢了。
而这位女修就倒霉了些.…以她这个姿势,就算想去拿腰间的信物都做不到。
对方似乎还怕荀妙菱不肯救她,急急道:“两位道友,我是青岚宗落霞峰的亲传弟子应山晴,我的宗门身份牌就掉在岸边,你们可自行查看。我以上三宗亲传弟子的身份保证,若你们能救我,出秘境后我愿给你们一人五百灵石!”
荀妙菱安慰道:“别怕,我来救你。”
“真的吗?太好了!”女修眼底的狂喜一闪而过,“对。只要你们能过来拉我一把.…”
接着,却见荀妙菱在四周环顾一圈,使唤飞剑削来一条结实的藤蔓,掐诀编成一个套索,然后抛向那女修,像是套娃娃以的把她捆住了。
被捆的女修:“”
苟妙菱甚至不必亲自出手,而是把藤蔓缠在息心的剑柄上,吹了个口哨:“来,三、二、一,拉!”
息心剑上的灵光一顿乱颤,以乎很不满意让它干这种牛马定位的粗活。但它还是配合着荀妙菱的口号,卯足了劲了往外飞。
眼看那条藤蔓被越绷越紧,那女修沾满泥泞的前胸以乎也从泥泞中被拔出一截来一但下一刻,“啪”的一声,藤蔓被崩断了。
女修重重咳嗽两声,神色愈加苍白。
荀妙菱看着那条藤蔓的断面,若有所思地瞧向那女修,面露难色。
她悄悄跟姜羡鱼道:“她到底有多重啊?怎么连飞剑都拉不动的。”
姜羡鱼瞥了那女修一眼。道:
‘人不可貌相。”
那厢女修已经在凄婉地哀求:
“两位道友,求你们御剑来拉我一把吧。再这么折腾下去我会沉得更深的。
的确,沼泽嘛,就是越净扎越深。
但荀妙菱偏偏犟上了。她喊来姜羡鱼用飞剑陪她一起拉,而且还削了三条藤蔓编成麻花做了个加固版绳套,再次往那女修身上一套,道:“别怕,大力出奇迹,这次一定行!”
女修的眼角一阵抽搐。
奇葩的是,一柄飞剑带不出她,连两柄飞剑一起还是不行。这回藤蔓倒是没断,但却在空中维持着僵持之势,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两方在拔河呢。
道友救咳”
突然,沼泽中咕咚咕咚冒出几个泡泡,那女修下陷的位置更深了一些,眼看就要没过她的脸。
荀妙菱叹息一声:“这下是不是不效不行了?”
她和姜羡鱼召来飞剑,飞向沼泽中心,向那女修伸出手。
女修苍白的面上一喜,也忍不住向前方伸出手去一突然,无数根粗壮的深绿色树从女修身后破土而出,如同一条条灵活的蛇,带着泥土的腥气和湿滑的触感,向荀妙菱袭来。
树藤的速度极快,几乎在瞬间就缠住了她的双腿,剩下的沿着她的身躯不断向上攀爬着,如一张劈天盖地的绿网,贪婪地向二人咬来!
那困在泥泞中的女修睁大眼睛,发出一声满足的喟叹,她湿长的黑发在瞬间化为一缕缕苍翠的绿藤,雪白的皮肤下好像有什么东西一阵涌动。
随后无数细密的绿色细藤从破皮而出,女修几乎在顷刻间就不复人形,而是成了一团上半身类人的、被树藤团团缠绕着的妖物一“新鲜的血肉。好香,真的太香了窥天镜外,很快有长老飞速认出了这妖物的真身:
“是木魅!”
“看它的根系如此之广,恐怕修为不止百年”
“千年木魅?那可是匹敌金丹中期的怪物啊!我们怎么可能这么多年都没有察觉呢?”
“或许这木魅的没有千年。”某长老皱眉道,“但它吞吃了足够多的修士以修士血肉为滋养,修为自然突飞猛进!
另一头,木魅惊奇地发现,它这回吃到了两个特别的修士。
即使身上被缠上了无数的藤蔓,但荀妙菱和姜羡鱼脸上也没有多少惊慌之色。
姜羡鱼:“玩够了吧?”
荀妙菱:“这也没得玩了啊。”
姜羡鱼叹息一声:“你的那叠火球符到底还是派上用场了。”
其实他们从踏入沼泽地开始,就已经感到了一股不对劲。
这附近盘踞着一只大妖。
而且一路走来,他们明明没有遇到什么灵兽,却在中途突然遇见了一群食人的鳄鱼。鳄鱼对人肉的渴望不能作假,但他们打了那么多只鳄鱼,却不见鳄鱼的血染红溪流的水,可见那些鳄鱼都是“假货”而已。
是这木魅有变化之能,操纵着树藤变化成鳄鱼,逼他们往这个方向走,引他们入沼泽的核心区域而已。
乍一见到这被困的女修,他们就直觉这是个陷阱。
果然如此。
只见荀妙菱略一挑眉,从储物法器中取出符咒,潇洒地荀妙菱抛向四周-一符咒在空中燃出一道道耀眼的轨迹,瞬间在水面上燃起熊熊烈焰,几乎将半片天幕都烧成红色。
火焰瞬间将眼前的木魅包围。木魅发出一声凄厉的哀嚎,触及火焰的藤条在高温的烧灼下瞬间枯萎成灰。
荀妙菱和姜羡鱼得了自由,御剑上天。
木魅:“别想逃!”
它的咆哮让泥沼激起巨大的波澜,声音几乎震动了整片树林。
无数绿色的藤蔓交缠,几乎编织出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向二人罩去。